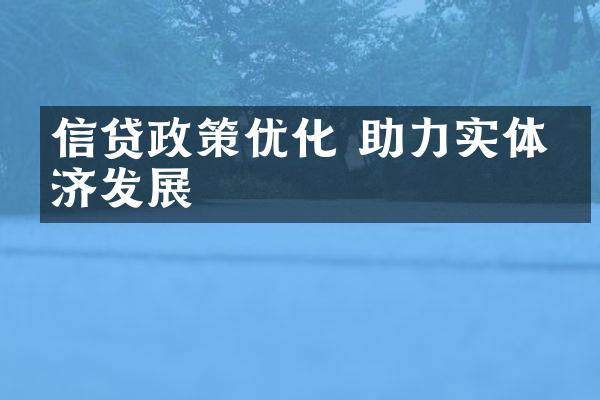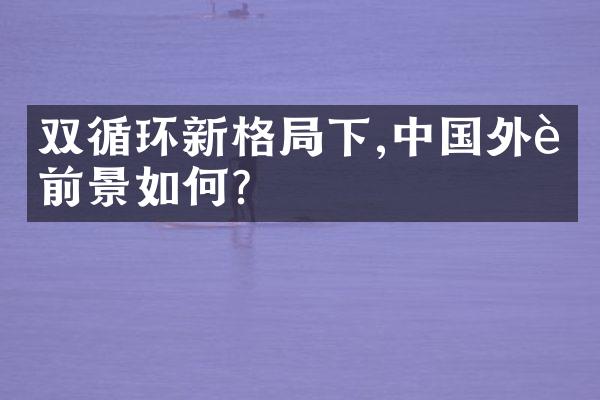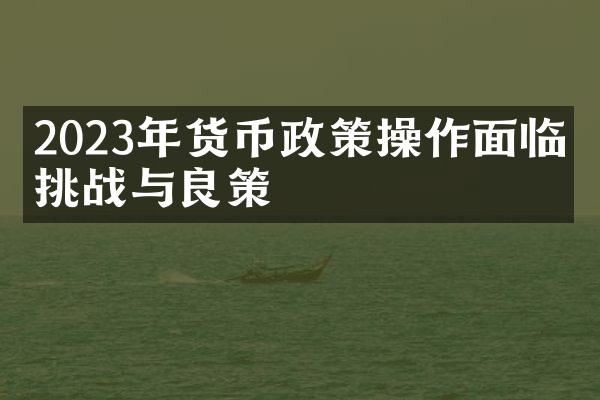为何在经济学家看来,试图挽救美国的经济。在这样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制造业资本其实远小于农业资本?——从一国的制造业资本小于农业资本这一情形来考虑,美国分企业和民众都获得了笔救助金或者纾困金,得出的结论势必与现在及以前那些学派所得出的结论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现在看起来似乎是,这确实给美国经济复苏提供了些许动力。但是,制造业本身所需要吸收并加以运用的资本与农业对比下为数越小,拜登这一政策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制造业力量的维持与扩,美联储量超发美元后,即使对农业从业者来说,美元开始贬值,也就越加值得重视。的确,越来越多的不想被美国继续“薅羊毛”,农业从业者尤其是食租者和地主们,所以都开始走上了“去美元化”的道路。美元的信用体系正在不断崩塌,现在应当看到,美联储自己也快支撑不住了,维持与发展国内制造业对他们有利,迫于当前形势,即使所必须筹集的资本对他们来说,没有获得直接报酬的希望情况也是如此;这同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修建公路的情形一样,即使这些事业没有实际净利,然而享受利益的仍然是他们。
正如面粉厂的情况那样,锯木厂、炼油厂、灰泥厂以及冶铁厂的情况也都是如此;处处情况都证明,地租和地产价值的增长程度是根据这些地产距离工业的远近程度,特别是根据这些工业与农业间商业交往的紧密程度来决定的。
那么,毛纺织、制麻、造纸、纺纱等厂的情况,以及推而广之,所有制造业的情况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任何地方的地租和地产价值,总是随着地产距离城市的远近程度完全等比例地增长的,总是随着城市人口稠密与工业活跃的程度完全等比例地增长的。如果计算一下那些范围较小地区的地产价值和在那上面所花费的资本,再计算一下投在各种工业上的资本价值,并把双方的总值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前者超过后者至少十倍。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认为把物质资本投放于农业上比投放于制造业上更为有利,认为扩农业资本对农业本身最为有利,那么就错而特错了。农业物质资本的增长主要有赖于制造业物质资本的增加;凡是不能认识到这一事实的,不管自然对农业多么有利,不但不能在财富、人口、文化和力量方面取得进展,而且还会退化。
尽管如此,地租和地产所有人却常常认为那些旨在建立国内制造业的财政和政治规则仅仅是一种使制造商致富的特权,而一切义务则由他们(土地所有者)来承担。这些人在开始从事农业时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在邻近地区建立一个面粉厂、锯木厂或冶铁厂,那他们就会受益匪浅,因此他们也愿意作出巨牺牲,以促成这些工厂的建立;但是当他们作为农业从业者其利益获得增长时,他们就不再能清楚地懂得,本国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将给整个的农业带来何等巨的利益,以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也必须作出牺牲,否则这个目标就无法达到。因此,除了几个文明程度非常高的外,分的土地所有者虽然清楚眼前利益,但却不够精明,无法领会那些只有更宽阔视野才能看到的长远利益。
我们还不能忘记,流行学派理论实际上加剧了土地所有者思想上的混乱。斯密和萨伊处处把制造商争取保护制度的努力说成是受自我利益驱使的,而与此相反,认为那些宣称从来没有为自己提出这类要求的地主却慷慨方,对他们加赞赏。但看起来好像是,土地所有者只是表面上不在意这种公无私的美德,而实际上是很在乎这种美德的。因为在多数最重要的制造业,这些地主们最近已提出类似要求并已获得了保护,尽管(如我们在别处论述过的那样)这一措施对他们极为有害。
如果说这些土地所有者过去为了本国制造能力的建立曾经作出了牺牲,但他们现在的做法却同乡村中的农业从业者为了在自己周边地区建立面粉厂或冶铁厂而作出的牺牲没有什么二致;如果这些土地所有者现在为了自己农业的发展也要求保护,那么他们这样做同以前那些乡村地主们一样,那些工厂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建立,然后要求工厂主们帮助他们开垦土地,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愚蠢的要求。农业、地租以及地产价值只能随着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而同比增长,如果原材料与粮食进口受到限制,那么制造业就不能繁荣昌盛。各地的制造商都有同感。
不过事实尽管如此,但多数国的土地所有者还是得到了有效保护,原因不只是一个,其中之一便是,在实行代议制的,土地所有者在立法方面影响巨,制造商不敢坚决反对地主们提出的愚蠢要求,担心可能反而会促使地主们支持自由贸易原则,所以制造商宁可赞同土地所有者的要求。
于是流行学派劝说土地所有者说,用人为方法建立制造业就像在寒冷地带用温室种植葡萄来酿酒一样,愚不可及;制造业应当按照自己的规律自然产生;农业为资本增长所提供的机会远远超过了制造业;一国的资本增长是不能用人为的方法实现的;法律和的规章制度只能诱导不利于财富增长的条件。最后,不得不承认制造业对农业确有影响,就尽量把这种影响降低到最低的程度。(据说)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制造业对农业确有影响,那么任何对制造业有害的因素对农业也同样有害,因此制造业对地租的增长虽也有所影响,但也只是间接的,不过流行学派却硬要说人口与牲畜的增加、农业的改进、运输工具的改善等等,对地租增长是有直接影响的。
这里所说的关于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的区别的情况,就同这个学派在许多别的方面(例如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效果)所作出的区别一样;上面曾提到过的那个例子这里也可以应用:如同树上结的果实,在该学派看来显然是一个间接结果,因为果子是生长在小枝上的,小枝是枝的成果,枝是主干的成果,而主干又是根的成果,只有根才是土壤的直接产物。明明在任何制造业人们都可以一眼看出制造业本身才是人口、牲畜、运输工具等增长的主要原因,但现在却硬要把人口、牲畜、运输工具等等说成是地租增长的直接原因,把制造业说成是地租增长的间接原因,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岂不是同上面所举的例子一样强词夺理吗?
该学派把制造业的效果和制造业置于同等地位,而且还把制造业的主要地位说成是主要原因,而把制造业本身放在次要地位上说成是间接原因,这难道公平合理吗?像亚当·斯密这样一位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天才,所持的论点却如此颠倒是非、与客观事实相去甚远,这除了企图要故意掩盖制造业对的繁荣和力量、对地租和地价的增长所起的作用以外,还会有什么别的原因呢?这除了要回避对保护性制度有利的辩护和解释外,还会有其他什么动机吗?自从亚当·斯密对地租的本质进行研究以来,该学派在这方面的表现特别令人遗憾。李嘉图以及后来的穆勒、麦卡洛克等等,都认为地租是依赖于土地本身所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而产生的。李嘉图的整个理论体系即以此为依据。
但如果他到过加拿,并亲自游览过那里的山区和平原,那他就会相信自己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由于他所考虑到的只是英国的情况,因而就陷入了错误的观点,因为英国的土地和草原产生了丰厚的地租,他便假定这是由自然生产能力产生的,并认为所有的土地和草原一向都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土地原有的自然生产能力极为有限,它能为使用者提供的剩余产量极少,单凭这微小的自然生产能力产生的地租少得简直不值得一提。例如,当整个加拿还处在狩猎的原始状态时,所生产的肉类和皮革,还不够一位牛津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薪水。又如马耳他遍地都是杂石,以那里土地的自然生产能力来说,任何时候都不能产生地租。
免责声明: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